甘孜日報 2019年0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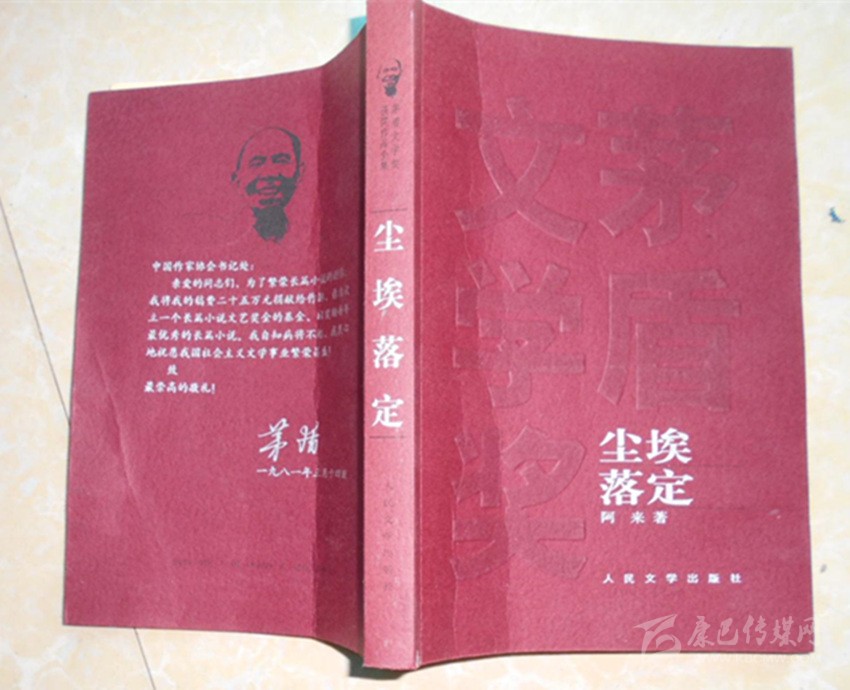
民俗文化集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于一身,是最具審美質素的生活文化。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那些優秀的稱得上經典的作品,幾乎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獨特敘事技巧相結合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關于阿來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持續性的話題,從《塵埃落定》 《空山》 《格薩爾王》等小說到詩歌、散文,都涌現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幾乎涉及民俗審美形態的各個方面。這些研究在不斷豐富阿來研究的同時,也在方法、方向上影響了對其他少數民族作家的研究,甚至是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作為少數民族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塵埃落定》在出版后的幾年內一度出現研究熱潮,但隨著其他作品的問世,近幾年關于《塵埃落定》的研究勢態漸弱。細數阿來的作品,民俗寫作一直在作品中占有相當的分量,因此,通過《塵埃落定》再思考民俗與作家創作之間的關系,在民俗審美性的層面深入挖掘民族精神的內涵,對民俗寫作和少數民族文學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也不失為少數民族文學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徑。
◎趙學勇
民俗:審美意識的個性化表達
有研究者將民間文化劃分為三個類型:農耕民眾創用的文化、城鄉中下層民眾使用的文化,以及審美創造中的民間文化。其中,審美創造中的民間文化是指融合審美主體的人格和理想之后,經過作家選擇和加工的民間文化。它是民俗在文學作品中最集中的體現,為作家自由表達理想心聲提供了審美空間。我們說,優秀的作品離不開對民俗風情的描寫,而民俗作品之所以富于魅力是因為它是“基于歷史事件寫成的風俗畫面。”作為青藏高原上“地標性”的精神建筑,《塵埃落定》是一部家族衰落、制度消亡的歷史,也是一部風俗史。阿來曾坦言:“我作為一個藏族人更多是從藏族民間口耳傳承的神話、部族傳說、家族傳說、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營養”小說中包括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藏族獨特的風土人情,神秘的民間禁忌、巫術、宗教風俗等在內的民間風俗是藏族人民歷經自然、社會、心理等各方面的長期考驗最終形成的獨特文化現象,它們內涵豐富、形態各異,是文本最基本的構成因素和審美質素,是小說進行人物形象塑造,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發展,小說民族特色等審美形態形成的重要推動力量。
民俗表現與人物形象塑造
文學是人學,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學的首要使命。尤其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民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著獨特的優越性,作家往往是通過對地方民俗的選擇與變形,將其作為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進而通過典型的個體人物來揭示人物群體身上的普遍特征。有研究者認為阿來“尷尬”的民族身份和“穿行于異質文化之間”的獨特寫作方式,使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漢藏文化交融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純正的“藏式”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實不然,我們應該認識到正是這種多民族文化影響下的寫作,才使得阿來能夠站在文化審美的制高點上,在對比漢藏民俗的基礎上,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態度尋求民俗文化與人物形象塑造之間的獨特視點,進而將兩者完美結合實現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塵埃落定》中的一系列活靈活現,生動有趣的人物形象正是出自這樣的審美情態。
首先表現在民俗化的稱謂上。名字本是具有指代性質的符號稱謂,當它與民俗文化結合起來時,就超越了本身的符號功能,成為帶有民俗性質的心理期待現象。尤其是在藏族文化中,起名是一件非常講究的事情,大多數藏族人的名字都借用佛教表示吉祥意義的詞。《塵埃落定》中,傳教者兼書記官的“翁波意西”人物設定的初衷是智慧的代表,歷史規律的預見者,其中“意西”在藏文化中有“傳教者”,“智慧的化身”之意;由于未成親就有了孩子而使孩子與自己成為家奴的母親給孩子取名“索朗澤郎”,“索朗”寄寓孩子的一生福德滿溢等,僅從取名上就能看出民俗對人物性格刻畫的功能所在,民俗化的稱謂似乎具有“聞其名,知其人”的功效,是讀者對人物最直觀的了解,卻往往能起到直達作品中心的目的。其次,肖像描寫是人物塑造最直觀的方式。《塵埃落定》中的肖像描寫避開了以往通俗意義上的從身材、容貌到表情、儀態的逐一刻畫,而是抓住富有特色的藏族服飾、禮儀來體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等級屬性。“騎一匹白馬走在一隊紅馬中間”,“巴掌寬的銀腰帶”,“累累的珠飾”,“新打的小辮油光可鑒”,土司太太貴族氣質的服飾裝扮與跛子管家的“破靴子”形成鮮明對比,突出人物的等級差異。為迎接茸貢女土司的到來,“我們”準備了盛大的迎客禮儀“大卷的紅地毯從樓上,順著樓梯滾下來。滾地毯的人很有經驗,地毯不短不長,剛好鋪到客人腳前”鋪地毯迎客是藏族獨特的習俗,“鋪地毯”說明客人身份地位的特殊,鋪地毯的行為發生在我看到茸貢土司的漂亮姑娘之后,使“我”好色的性格特征躍然紙上。此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離不開“詩畫合一”的環境氛圍。小說在“下雪的早晨”,“野畫眉的聲聲叫喚”的美景中開始,先后營造了春日耕作、罌粟遍野、冬日雪景等圖景,使得歷史敘事小說帶有抒情詩般的境界,為人物出場營造了氛圍也推動人物性格走向成熟,“我”就是在這些場景中,從最初愚鈍無知的“傻子”成為勇敢機智、名利雙收的新土司的。
民俗文化推動故事情節發展
民俗在文本審美中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民俗是文本敘事的重要一環,具備民俗敘事的作用,也就是“將民俗按一定的敘事邏輯納入到前后推進的情節鏈之中,使其成為小說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基本環節,推動并影響情節鏈”由于在文字發明之前,主要靠口耳進行文化的傳承,所以藏族民間口頭文學很興盛。民間歌謠作為口頭文學的一個重要類型,在《塵埃落定》中前后出現了八次,幾乎每一次緊張、帶有懸念的故事情節,都伴隨著民間歌謠的出現。麥其土司種罌粟的第一年,發生地動。小孩子們“國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徹底碎了”的歌謠,與到處漫游的蛇,濟嘎活佛的寢食難安一起,作為地動的先兆現象成為故事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鏈接點。因為歌謠多是由民間故事改編而成,所以在內容表達上與小說情節緊密銜接,形式上的對仗、押韻特點,又具有情感表達、溝通交流的作用。此外,部分民俗文化的制約是小說情節沖突形成的基本點,而矛盾沖突又成功推動了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對于民族群體而言,民俗制度的形成是一個長期往復的去粗取精的過程,新的異質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的進入,往往會與舊的制度規范形成沖突。“傻子”不合常理的做事方式與土司家族千年不朽的家族制度就構成了小說中主要矛盾的兩面。在奪權與棄權,故步自封與發展邊境貿易,鼓勵戰爭與主張和平等沖突中,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民俗風情強化文學的地域特性
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民俗是一個地方生活樣貌的集中展現,藏地小說的民俗風情突出表現了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就地理條件而言,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地處亞歐大陸的中部,藏族原始先民為適應這種海拔高、氣候寒冷的惡劣自然條件,在房屋建筑、飲食習俗、服裝配飾等方面做出相應調整,日積月累,久經歲月洗禮,形成藏族今天的風俗樣貌。藏族主要以畜牧業為主,因此飲食多以牛羊肉及牛羊乳制品為主,從“整只羊下到鍋里”,“茶水飄出香味”,“油鍋里起出耳朵形狀的面食”,“暖身的酥油茶”等飲食習俗看出地理上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民俗上的獨特性。藏袍是藏族的主要服裝,肥腰、長袖、大襟、右衽,主要由牦牛皮制成,設計簡單,講究邊飾,衣袖、衣襟,衣底常會鑲上貴重的毛皮和絲綢滾邊。碉樓和民居是藏族最常見的兩種建筑。《塵埃落定》中麥其家族的官寨屬于高碉建筑,一般人則住在石頭砌成的兩層碉樓里,上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這種“人畜結合”的特征明顯突出了藏區以畜牧為主的地域化特點。
藏族生活中的部分民俗事象與佛教的精神旨歸之間有著一定的相通性,藏族忌食狗、馬、驢、騾、蛇、鼠等動物,因為受佛教“忌殺生”思想影響,“母親正齜著雪白的牙齒撕扯鼠肉” 的場景引“我”惡心。在葬俗上,與漢族入土為安的習俗不同,藏族以天葬、水葬、火葬和塔葬為主要葬儀,其中以水葬、火葬最為常見,奶娘德欽莫措夭折的孩子由喇嘛們念了超度經,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戰爭過后,給陣亡者舉行的火葬,麥其土司的大兒子被復仇者殺害后,麥其家族為其舉行了隆重的火葬儀式,藏族人民多是通過“水”“火”渠道讓逝者肉體回歸自然,以追求生者精神和心靈上的“凈”。可以說,宗教因素是民俗形成的重要原因,不同地方的民俗,因自然環境、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千差萬別。誠然,民俗寫作在深化文章主旨,觀照文本的文化情懷等審美形態方面,都有重要的價值意義,但民俗的價值絕不僅僅表現在文本的審美價值上,透過民俗,深入挖掘隱藏在民俗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寫作的另一重要意義。
民俗:民族精神的集中彰顯
民俗是作品民族特色的外顯符號。一般而言,注重對民俗文化運用的作家,常帶有強烈的審美超越意識,他們關注社會轉型中人民大眾的生存狀態,關注民俗文化中有助于民族精神建構的事象,注重對生命意義的闡發,認為通過民俗寫作來揭示民族文化精神,才是民俗寫作的意義所在。阿來正是想通過民俗寫作,讓人們知道,我們所謂的藏族文學,絕不是已經在讀者潛意識中形成的,簡單地展示雄偉壯麗的高原美景,展示神秘古老、飽經風霜的藏族生活的“圖景式”文學,而是關注在青藏高原這塊廣袤、厚重的土地上,在相對處于劣勢的自然、社會條件下,藏族這一群體的生命歷程,體味在神圣宗教信仰的支撐下,歷經自然磨難、歷史洗滌的,在絕境當中磨礪而成的戰勝苦難逆境,敢于挑戰的堅毅品質和民族精神。
其一,狩獵民族的“英雄主義”本質。從地理板塊構造上來說,青藏高原曾經是汪洋大海,隨著地殼運動,在板塊動力的作用下,形成今天山峰聳立、冰雪覆蓋的壯麗美景。自然,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壓低、干旱少雨的氣候特點,不適合發展農耕經濟,藏族先民們為維持生存,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方式,原始農耕經濟被畜牧業和狩獵經濟所取代。長期以來,面對地震、雪崩、火災等自然災害以及外族入侵、邊界戰爭等人為災難的雙重威脅,藏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生存的不安感和脆弱感,加之,長期與牲畜共存,與野生猛獸斗智斗勇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現,使他們形成對救助首領、英雄人物的期待心理。因此,對英雄人物的呼喚,是當代藏族文學的精神取向之一。《塵埃落定》中行刑者爾依父子的忠誠,奴仆索郎澤郎視死如歸的行者風采,多吉次仁的兩個兒子為父報仇的忠志不渝,麥其土司的開放樂觀、威武勇猛、野心勃勃,麥其大少爺威風凜凜的英雄無畏,都是在社會轉型期,面對人文觀念、經濟發展方式、生存制度等的改變,茫然無措的藏族人民生存和發展需要依賴的民族精神。這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面對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快速發展,在新舊觀念的激烈沖突下,其他民族所面臨的共性問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英雄人物的領導,社會各行各業的發展同樣需要精英人才,無論何時,呼喚英雄人物都是時代發展永不過時的主題。
其二,多樣人倫中對至美人性的追求。將多樣的民俗風情和宗教信仰融入創作中,塑造出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從善惡美丑不同角度對人性加以呈現是民俗文學常見的審美形態。《塵埃落定》通過民俗寫作塑造了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專制斂財的麥其土司,勇敢剽悍、聰明神武的麥其少爺,智慧使者翁波意西,視財如命的黃特派員等不同的人物代表了人性的不同層面。不容忽視的是,這些人物形象都是為“傻子”這一中心人物服務的。“傻子”形象來源于藏族民間故事中的完美人物原型“阿古頓巴”。雖然“傻子”具有病理意義上“傻”的全部特點,但是他具有超越時空、預見一切的能力,具備異乎常人的情商。在等級差異面前,他同情弱者,面對困難,他積極豁達,他潔身自好,不染毒品,他能夠機智地看清每一個人,看透每一件事,他能看到土司制度即將消亡的事實,也能勇敢接受現實,迎接挑戰,積極發展邊境貿易。“傻子”形象具有“人性至美”的完美品性。在時代發展的今天,飛速發展的經濟、科技使藏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受到強烈沖擊,人們精神的極度缺鈣,需要從根源上尋找人性最本真的東西,需要至美的人性來填補心靈和精神上的缺憾。“傻子”形象的出現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物質需要和精神價值之間的沖突,歷來是人類群體所面臨的共性問題,在追求物質進步的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精神的重要性,應該從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出發,追求人性的至美。其三,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民族品性。青藏高原很多地區的經濟主要依賴狩獵和放牧,牧民對草原和牲畜的依附感特別強烈。藏族信奉山神,禁止亂砍亂伐,因為長期以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對自然有著別樣的理解和感受,他們相信人從自然中來,人的生存需要從自然中索取資源,大多數藏族人去世后選擇水葬,將自己交予自然,大自然在他們生命中是最神圣的存在。藏族忌食狗、馬、驢、螺等動物,因為長期的游牧生活,稀少的居住人口以及內心積蓄已久的孤獨感使得他們與動物之間形成最緊密的聯系,他們依賴動物,馬、驢、螺是出行必備的交通工具,狗是最忠誠的伙伴,加之酥油茶、糍粑、牛羊肉、牛羊乳等飲食都產自牲畜,所以他們與牲畜之間有著最特殊的情感。在這種依賴感的驅使下,對自然的尊重和生命的敬畏成了民俗精神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時至今日,藏族人民仍然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念最忠實的踐行者,這種因民俗而形成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緊密聯系,是促進我們整個民族持續發展、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最后,“家國同構”式的民族凝聚力。《塵埃落定》是一部家族制度的消亡史,也是藏族內部族群的生存抗爭史,不同的部落為了生存,表現出強大的超乎想象的族群凝聚力。麥其土司為了強大不衰,團結一心擴張疆域的豪氣,波斯使者為了家族強大視死如歸的凜然,讓我們對民族生死面前,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望而生畏。這樣的民族精神在回、維吾爾、蒙古等其他少數民族那里同樣具有普遍意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家族母題為內容體現民族凝聚力的作品不在少數,《心靈史》 《穆斯林的葬禮》等都是民族為了生存不屈抗爭的血淚史。作為抽象的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具有“家國同構”的性質,各個民族為了生存所表現出來的集體向心力,匯聚在一起就形成了集體的凝聚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與國是根與葉,存亡相依的關系,尤其是對于我們多民族國家來說,國家的繁榮昌盛、興旺發達離不開各民族的共同發展,離不開民族凝聚力的支撐。
總的來說,古老豐富的民俗信仰和艱苦險惡的高原環境相結合,鍛造了藏族人民堅韌的民族品格,形成了藏族精神的核心內涵,那就是對自然生命的敬重,對至美人性的追求,同命運抗爭的頑強,為信仰誓死前行的悲壯。開放與內斂并存,達觀與憂患并重,堅韌頑強、樸素厚重的生存精神,以及執著堅守,勇于奉獻的社會責任感。這樣的民族精神,是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全民族所需要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強大民族精神的支撐。如是,發現、抒寫民俗文化,將民俗精神發揚光大于文學的作用正在于此。
顯而易見,以阿來為代表的民俗創作,不僅僅是對民族精神的彰顯,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正基于此,研究當代藏族小說與民俗文學之間的關系,以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為摹本,結合民俗的文本表現和人們行為的實際表現,發掘藏族文化精神,并由此普及和影響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對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維持民族文化的長久發展,實為有效途徑。